在戏谑中深嵌着严肃的意图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慢》
刘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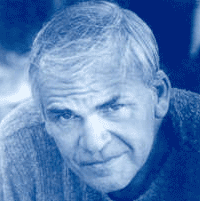 《慢》是一部情节简单、风格飘逸、且又含义深邃的小说。为数不少的人物随意出没在文本中,犹如幽灵;伴随着思性笔调似被风吹散的花瓣洒落在内容四周;论述穿梭其中,既像点缀在叙事周围的花饰,又像推动情节潜行的滑轮。它在文本中镶嵌着另一文本,时空交叉,相互缠绕,使小说变得意义暧昧而又难以复述。只是到了最后一刻(20世纪的某个清晨),小说中不同时代的人物才共同定格在一座古城堡的花园小径上——时空弧弦上的一个交汇点——才使小说显露出它的深刻的涵义。
《慢》是一部情节简单、风格飘逸、且又含义深邃的小说。为数不少的人物随意出没在文本中,犹如幽灵;伴随着思性笔调似被风吹散的花瓣洒落在内容四周;论述穿梭其中,既像点缀在叙事周围的花饰,又像推动情节潜行的滑轮。它在文本中镶嵌着另一文本,时空交叉,相互缠绕,使小说变得意义暧昧而又难以复述。只是到了最后一刻(20世纪的某个清晨),小说中不同时代的人物才共同定格在一座古城堡的花园小径上——时空弧弦上的一个交汇点——才使小说显露出它的深刻的涵义。
“我”(一位作家)偕妻子薇拉前往一座现已改为旅馆的古城堡度假。“我”驾着车缓慢行驶在公路上,不时有汽车和摩托超越而过,这引起“我”对现代速度的思索,并联想到另一次也是从巴黎出发去乡间城堡的旅行——那是发生在两百多年前的某一天,T夫人和陪着她的青年骑士坐着马车前往巴黎的郊外城堡。“他们第一次挨得这么近,笼罩在他们四周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性感氛围,正是由于一路上慢慢悠悠引起的。”这是18世纪法国作家维旺• 德农小说《明日不再来》中的内容。
一路上作家思绪飞扬,除了联想到T夫人的故事外,他还在构思着自己的小说。到城堡后,他一夜未眠,继续沉浸在遐想和小说的酝酿中:20世纪的某一天,一群昆虫学家聚集在相似的变成旅馆的城堡内开年会,他们在城堡内发生不少可笑的事情;期间还插入了学术表演家贝尔格的无知与作秀、电视台女导演自恋式的偏执追求、捷克学者的迂腐忘词、文森特与女打字员的调情等等事件,以及18世纪的T夫人与骑士的馨香幽雅的风流韵事。妻子薇拉的睡眠数次被打断,因为作家头脑中这些时代混杂的人物闯入了她的梦而受到惊扰。“你是我深夜写作的受害者”,作家抱歉地对她说。
第二天凌晨,薇拉醒来后立即嚷着要回家。“这座城堡闹鬼”,她说。清晨,作家和他的妻子坐上汽车准备打道回府,薇拉在发动汽车,作家指着车窗外对她说,“等等,你看!”他们看见花园小径一侧骑士辞别了T夫人正走向马车;昆虫学家文森特戴上头盔在发动他的摩托车。
真是令人惊讶的一幕!这一刻如同一面魔镜将作家头脑中的虚幻的不同时代的人物的身影同时映显而上,并与他们的虚构者(作家)和旁观者(薇拉)相会于此。这犹如梦境,所有的人不受时空限制地在“现实”中交汇;犹如打开了一天一夜的扇面在这一刻突然合拢,而扇脊的两侧则是整整两个时代的趣味的反映。
作家走进正在构思的(同时也是我们阅读的)小说中“观察”小说的进程,他的妻子(确切地说也是小说中的人物)也参与了这样的“观察”行为。昆德拉刻意这样安排,是要表明小说的不确定性,构思中的小说就犹如一个“仿佛”——仿佛小说可以随时可以被改写似的。作家(小说中的“我”)在观察自己头脑中的人物的行为,但他又被其背后的作家(昆德拉)观察着,这种双重的虚构,其真正的意图是要让小说的能指漂移,让人物形象尽可能地走向文本的边缘,充分调动起暗示作用,使文本显露出比自身含义更为丰富的意义。
从这意义上说,《慢》是一部元小说,一个尚在构思途中的小说拟本,一个文本游戏。作家走入自己的小说中,表面上似乎是为了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而实质是要让“作家”作为一种媒介,使两个时代的人物能够自由对话,显示他们的差异性,使能指分裂、变幻,最终演变为不同时代的象征符号。因此,小说的主导动机是要挖掘两个时代的不同趣味,反映两种时代的风尚,从而进一步嘲弄在当今时代的快节奏中人性扭曲的现象。
小说中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物,对时间的消费概念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异,这就如同托马斯•曼《魔山》中的“山上时间”和“山下时间”那样迥然相异。这一夜——在相同的时间单位里——T夫人和年轻骑士从容地、优雅地调情,他们在花园中漫步,述说喃喃情话,让“事件”一波三折而又有序地深入,最终到达了佳境。对他们来说,“天亮”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他们并不急于要履行完所有的“仪式”。他们要的是让“事件”进行得完美,并在记忆中刻下永恒的印记。
而对文森特来说,这一夜则显得匆忙和可笑。他从会议中溜出,在酒吧里与大会秘书处的女打字员调情,一边又心不在焉地注视着酒吧另一侧的同行们,他的调情行为像是故意要“表演”给他们看似的。期间他在取酒时被同行奚落,他耿耿于怀,使高昂的情绪和蠢蠢欲动的念头一落千丈。为了完成已开始的调情,他建议与女打字员一同去游泳馆裸游。此时,就像一出演砸了的戏一样,他只得与期待以久的女打字员在池畔做爱,但可怜的文森特却力不从心了;期间又被另一对争吵的情侣撞见,他们慌忙中狼狈而逃,祈望人们尽早将他们遗忘。破晓时分,文森特无心同任何人告别,趁人们还在酣睡之际匆匆离去。
这里,昆德拉在描写T夫人同骑士的情爱故事中赋予了她充分的自主意识:她明了自己要什么,懂得如何让“事件”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并不时调整策略,让“事件”进行得更完美,更富有情趣和诗意。文森特则相反:他像一辆向前冲刺的汽车,他“发动”了它,然后身不由己地被惯性推动,最终连方向都无从把握。昆德拉把小说中的人物喜剧化、寓言化了,其重点不在于人物行为的可信度上,而在于情节所包含的意象和象征性上。
小说通过两个时代中的人的不同行为方式——一种具有内在自主性;另一种仅仅只有外在的虚设行为——的对比,来对现代机械社会造成的人的自主能力的丧失现象进行了调侃。现代机械时代提升了速度,却也使人在追求速度的快感中迷失了自我和失去了方向感。人们一味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奔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无暇顾及自身的位置,他们惟恐被时代抛弃,真正所惧怕的不是速度本身,而是被搁置或遗弃在速度之外;至于在速度中有没有自我存在的价值和反思自身存在方式的能力则无关紧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间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它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影子,人是其中是摆渡者,自身的偶然性与摆渡间的关系的确立才使时间的虚幻性显出了意义,从而使人的存在确立了价值。因此,一旦在时间流动的虚无中不能感知时间,确立自身的价值,那么,这无疑是陷落在一种双重的虚无中。
米兰•昆德拉在《慢》中,将两个时代的人的不同的时间意识做了对比:悠缓的古典主义和高速的现代主义,它犹如一首乐曲中的第一呈示部和第二呈示部,并在 “慢”、“快”、“慢”、“快”的奏鸣曲式的节奏中进一步变奏出“记忆”和“遗忘”的主题。在昆德拉的词汇中,“慢”形成“记忆”;记忆不仅让人们在事件消失后仍能继续在心中留有回味的余韵,还在于使事件的意义增殖,以回溯的想像方式进一步扩展它的空间。相反,“快”则造成“遗忘”;遗忘是让事件的意义“空白”,是使人们在虚妄中再度“抹杀”自己。
不可否认,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以及情节的设置上均作了略显夸张的处理,他以微带漫画似的笔触将人物的某些行为推向了极致,其中显示了作者对他们行为所进行的尖锐的嘲谑和挪揄。他这样处理,纯粹是以一种游戏的方式来包装他小说中的严肃的主题。他试图以幽默方式对现代人的愚蒙行为进行一次反讽式的拯救。
《慢》以及后来的《身份》、《无知》是米兰•昆德拉流亡法国多年后相继用法文撰写的小说。相比他的“捷克时期”小说,我个人认为,他的“法国时期”(姑且这样称之)小说摆脱了、或者说虚化了他“捷克时期”小说的政治意识——尽管他否认自己小说具有的政治涵义,宣称“小说是被道德悬置的领域”——关注一些更为普泛的问题,诸如时代的变化与背谬、人性隐秘的本质、人的无根与漂泊状态等,着眼的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某个特定政治区域内引发的问题。
因而,他的“法国时期”小说不像他“捷克时期”的小说那样凝重阴郁;相对来说,“法国时期”小说篇幅更为短小,风格更为飘逸、深邃,笔调更为轻捷、敏感,结构更为精致、丰盈,犹如诗体中的十四行诗那样,做到主题凝练,在有限的架构内尽可能地包含丰富的内涵和令人回味的外延。
版权所有 游吟时代 保留全部权利 © 2003-2013 Youyin.com